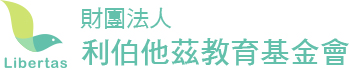文/社資實習生
在正式進行學員美術課程之前,我其實對這些即將見面的學員,抱持著相當多的想像與不確定。雖然身為社工背景的學生,也曾經一再地學習要跳脫對藥癮者或更生人的社會污名,知道不該用「壞人」、「可怕」、「難以親近」這些標籤來定義他們,但當我第一次以講師的身份站在他們面前時,心裡還是忍不住緊張——擔心自己會不會招架不住、會不會被質疑,甚至會不會被挑釁。
坦白說,我一開始還是帶著一點社會大眾常有的刻板印象。腦海裡浮現的,是影劇或新聞裡那些眉頭深鎖、面色冷峻的樣子。我以為他們會沉默、抗拒、不想配合,甚至可能在課堂中表現出攻擊性或冷漠。我做好了心理準備,也預演了好幾套「如果他們不理人、或者直接走人,我該怎麼處理」的情境。但出乎意料地,真正的相遇竟是那麼輕盈與自然。
第一次上課那天,學員們陸續走進教室,很多人一進門就主動和我們打招呼,語氣裡帶著一種熟悉感和親切。他們彼此開著玩笑,也不吝嗇在我們講話時插科打諢。有人問:「老師,你們怎麼那麼年輕?」雖然語氣略帶挑釁,但說完就自己笑了出來。還有人一邊搓著黏土一邊說:「我小時候也愛玩這個,今天終於又有機會玩回來了。」我才發現,原來我以為會很難親近的「他們」,其實只是一些有著豐富人生故事的「老頑童」罷了。
他們在課堂上的模樣,和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。他們會因為作品成功被稱讚而露出孩子氣的笑容,也會因為黏土沒捏好而故作氣惱地拍桌子。他們會問我們:「這樣擺好不好看?」也會互相比較作品尺寸大小,一邊鬧著要換位置一邊笑得合不攏嘴。有時我們還沒開始說明流程,他們就已經自顧自地動起手來,一副「我很有經驗」的樣子。那一刻,我心中某個很深的防備感被鬆動了。
我看見他們的創作,也聽見他們在創作中的對話,他們談起過去,語氣裡有懊悔,也有一種說不清的釋然,他們並不是冷漠的,也不是難以親近的。他們只是經歷了我們難以想像的人生故事,在時間的洪流中被捲進漩渦,跌撞過、錯過、痛過,但當你真正坐下來、和他們一起捏著黏土、畫著顏色,你會發現他們內心其實仍有柔軟的部分,仍有渴望被看見與理解的那一塊。
身為講師的我們,其實並不比他們年長太多甚至大多數的學員都比我們年長許多,但在課堂上,我們獲得了他們的尊重,也收穫了許多讓人動容的回饋,有學員在第三週分享作品時說:「謝謝你們設計這些課,讓我想起我還有手可以做些不一樣的事。」這句話我一直記到現在,他說的不是技巧,而是重新發現自己還有能力創造、表達、觸碰記憶,那一刻我幾乎想哭——因為我們的用心真的被感受到了。
這三週的課程,是一段彼此認識與理解的歷程。原本我以為我是來「教」的,但最後回過頭看,我卻從這些學員身上學到了更多,我學會了什麼是打破標籤,也學會了什麼叫真正的平等對話,我再也不會用「更生人」「藥酒癮者」這些字眼去預設他們的樣子,因為我知道,在那些標籤背後,是一個個會笑、會玩、會表達、會難過,也會重新站起來的「人」。
他們其實與其他人無異,他們也有喜歡的事物,也有做過錯事的過去,也有想要重新開始的願望。如果世界可以多一點空間給他們,或許他們也可以少走一些彎路,我想,這個世界的改變,就從我們不再害怕接近他們、不再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開始吧。